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点击上方“独立精神”可订阅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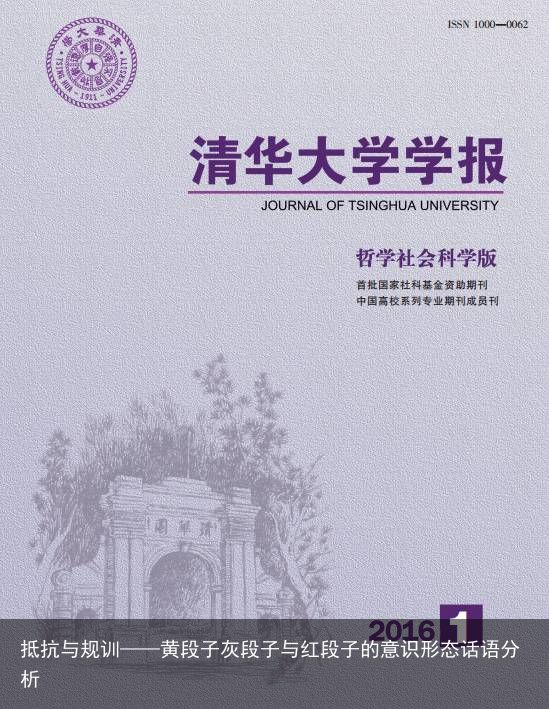 摘要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关键词 黄段子;灰段子;红段子;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作为俗文化中最为贴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间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来以旺盛的生命力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近些年,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互联网的发达以及新兴便捷媒介手机、ipad等的勃兴,段子文化成为一种蔚为奇观的大众文化现象。然学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与政治等敏感话题而研究的不多,隐隐体现出一种不敢、不愿或不屑的心态。而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红段子”的言说,学界则普遍表现相对踊跃。较早从学术角度论及段子的是2008年《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上的一篇《段子管窥》,该文对段子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广义的段子,指的是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赏的、简短自足的或长篇中可独立出来的短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话、小品,也可以指戏剧中的唱段……狭义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尤其指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幽默类的故事、笑话、脱口秀、顺口溜等……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亦采用这个界定,所论的段子属于以上所说的狭义的段子。将近年流行的各类段子以颜色分为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等,既体现了人们对段子内容的区分也体现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简言之,黄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为话题及取笑对象的段子,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灰段子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抨击时弊或表达现实无奈的自嘲的段子,体现出一种灰色的心态或黑色幽默的特点;红段子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制作、传播的一种代表健康社会心理、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短信息文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与民间自发流传的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民众的精神空间,打击黄段子灰段子所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在段子的喧哗世界里,很典型地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和博弈。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这两大类具有对抗性质的段子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无意识和意识形态企图。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以上溯到20世纪文学批评中以文学的话语方式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这一传统摒弃了过去文学批评以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意图的臆测、抽象的美学特征、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而转向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进行“症候式”的阅读,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话语分析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多数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人民“真实”的情感表达,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对统治权力的某种抵抗,大众文化是差异文化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什么是大众文化,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按照这个界定,中国内地近年流行的民间段子完全具备大众文化的特点,而且在表达的内容、创作的方式、传播的途径、意识形态的诉求等方面,比一般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如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更具有“大众”的身份和特点。因此,我们对当前大众文化中的这种代表形式——“段子”——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性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一、抵抗与消解要理解民间段子所表达的平民意识形态诉求,最好的方式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间段子(本文主要指黄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何以在中国内地盛行的原因。关于盛行原因,目前学界相关说法一般都比较务实,如《段子管窥》认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餐文化的消费;具有高度的娱乐性。《“黄段子”为何流行》认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绪放松的快乐,三是交友的需要。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娱乐、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艺术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与今天的段子内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艺现象,都可以说也具有以上所说的功用。明末冯梦龙《挂枝儿》《山歌》和《广笑府》里收集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行“歌曲”和笑话有很多就属于今天理解的黄段子和灰段子。仅举几例:牙刷儿,身材短,刚刚五六寸,穿一领香喷喷绿背心。一条骨子儿生成的硬,短鬅松一搭毛儿黑,光油油好一个下半身。专与那唇齿相交也,(每日里)擦一阵儿爽快得很。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根头。姐道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铁线身粗慢慢里抽。姐儿生来像花开,花心未动等春来。囫囵囵两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里含羞夜里开。一僧读“齋”字,尼认是“齊”字,因而相争。一人断之曰:“上头是一样的,但是下头略有些差”。或问好色者曰:“世间何事最乐?”答曰:“行房最乐。”又问:“既行房后,还有甚乐?”沉吟曰:“除是再行。”官值暑日,欲寻避暑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凉。一皂隶曰:“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问其故,答曰:“此地有天无日头。”前面几则或隐或显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段子,其中第5则在当下被改成湖南或四川方言再次在民间流行(只是把“行房”改为“做爱”,最后一句改为“再做一次”)。第6则对有权者的讥讽则类似于今天的灰段子。如果单从民间文艺的一般功用角度来分析流行原因的话,似乎无法解释民间段子为什么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一层的追问,即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大量需要段子来消遣、娱乐、宣泄、交流?冯梦龙收集的这些大量涉及私情、欲望的民间“段子”在当时的盛行原因或可资参考。涉性的民间原生态的“段子”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只是过于“俚俗”“粗鄙”而不被文人收录和记载,它只能潜流于生活的当下,由于没有资料记载,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现冯梦龙这样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段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类似“段子”的大量流传。明末市民社会发达,民众的娱乐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于引起文人的关注,甚至介入收集、仿制和传播的行列;另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与当时新兴印刷技术的大众化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明显地强调其传播的“大众”、“消费”的媒介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民间段子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发达产生了其广泛的受众,最为关键的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明清时期的刊刻造纸技术对俗文化的推动一样,近年国内民间段子的盛行与新兴的互联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手机短信平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电子传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广,使民众广泛参与、广泛传播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传媒交互平台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欢迎,客观上引导和鼓励了人们进行碎片式(“段”)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的审美体验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的红段子也正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平台得以顺利有效施行的。第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涉及民间段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所承载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识形态诉求。尽管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但民众对转型期内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感受深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转折点在近一百年来并不多,历数起来大致是“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效应上近年表现逐渐明显。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商业浪潮和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切身体验,并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普遍的表达。与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相比,世纪之交前后的这20来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现代性体验。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很像西方社会之前经历的那种转型,只是我们在时间上滞后了而已。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些年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但有些地方用来形容中国社会近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亦有相似之处。如商品经济浪潮的推拥裹挟、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等都给人带来普遍的变动感,尤其是在这个急剧转型中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似未成熟——这从近年来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这一点给人带来很多的迷惘和焦虑。人们处在土地征用、拆迁、城市化等空间的迅速转变当中,处在拼命追赶“与时俱进”的各种不确定的事物变化当中,处在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失范诚信缺乏的危险境地当中,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浮躁和戾气当中……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总结回顾中,“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反观自身的时候,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种短平快且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俗文化形式——民间段子——在新兴电子传媒的推动下蓬勃兴起,人们在这些充满戏谑、狂欢、讽刺、自嘲的话语中深获共鸣。由于民间段子结构的松散性、主题的随意性、艺术的通俗性,几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创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衍化繁殖,体现出集体的智慧与趣味,再通过能够迅速传播的公共传播手段,使得人们同声相应,手、口、耳相传,最终形成一股全民狂欢的风气。在这种文化狂欢的背后,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无意识和平民意识形态的诉求,包含有一种无声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对权力压抑的消解。这可以从民间段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从内容上看,黄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与性器,带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话以及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的嘲讽。性与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属于禁忌的话题,禁忌的内容、禁忌的惩戒,意味在此之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力和制度权力。冲破这些禁忌,意味着一种抵抗和解放,并因此获得某种匿名的快感。这一点很像西方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的摇滚乐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摇滚乐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摇滚乐却得到不少赞赏,甚至文化研究的论者还把摇滚乐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摇滚乐的粗鄙、炫耀式的“堕落”,狂欢化和快感原则,甚至它的命运和遭遇,都跟黄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摇滚文化只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和肆无忌惮的“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话,中国近年盛行的民间段子则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狂欢文化。约翰·费斯克在论及大众文化的资本时曾指出:“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按照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权力给人的快感是双向的,“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无权的大众阶层很多时候喜欢通过低俗、鄙俗甚至淫秽的黄段子对道德话语权力进行挑战,以粗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带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意味。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使黄段子的讲述者与听众体会一种充满“机智”“巧妙”的创造性反应,获得“狡黠”“恶毒”的快感。如:一男子到医院做非典检查,护士取针刺手指为其验血,因一时没棉花,情急中护士赶紧将其手指含入口中。男子痴迷半晌后款款的说:我想再做个尿检。乡长穿着短裤作报告,讲到激动时把一只脚抬放在椅子上,小弟弟露了出来,会场一片哗然,他以为大家不耐烦,就大声说:这只是个头,后面还长着呢!以上几个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种符号,它不是叙事意欲突出的内容,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使叙事的氛围变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话语权力的整体沦陷中人们觉得亲密无间,有一种集体抵抗同一战线的快感。又如:政府做完工程却省下一大笔钱,于是众人开会举手表决。是把这笔钱拿来改造中小学还是改善监狱环境。会议分成两派,众人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老常委一语定乾坤:“你们这班子人这辈子还有机会上中小学么?”顿时众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决定改善监狱环境……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辨别真正成功人士: 1.没有名片;2.自己不开车;3.衣服没logo;4.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5.每天午睡;6.经常在郊区活动;7.包里现金很少……旁边一位农民兴奋地打断:“这种人,我们村全是!”以上两例是灰段子的常用叙事模式,用强烈的反差造成反讽,对权力符号的揶揄和解构,在听众的哄堂大笑中神圣、庄严的东西轰然倒塌。无权无势无财的大众在一无所有中往往只能通过灰段子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讽刺以及对权力符号的消解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嘲弄腐败官员、为富不仁的富贵者(他们一般被符号化为“贪官”“煤矿老板”“暴发户”等)的愚昧、无能、丑陋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体会一种对原权力进行嘲弄的权力,产生一种“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并“证实自身”,产生一种阶级认同,获得慰藉和温暖。这种精神胜利快感的表现形式在于民间段子独特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中激赏拉伯雷在笑谑民间文学收集和创作上的成就,他说:“人们一般提及,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性的地位。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 因此,拉伯雷被不少人指责,但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的、“鄙俗化”的风格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及民间获得解放的力量。而广场言语和狂欢化是民间笑谑文学的话语特点,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日常的、亦即非狂欢的生活中,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在这里)异化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群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 在论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阐发道:“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这种笑声是个矛盾体,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解放性)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现象的雏形——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段子所具有的广场言语和狂欢化的特点,决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种纯粹提供给人阅读的文本,其效果往往需要话语的讲述来呈现,具有一种“在场”性和“表演”性。“在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段子的讲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会上、旅行团的车上,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如网络论坛、QQ群、微信朋友圈等),起到一种交往和聚众狂欢的效果。“表演”性表现在讲述的时候注重模仿(行动、语气、口音等)、注重互动和即兴发挥。尽管很多民间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传播,但也只是为了扩散,作为聚众时候讲述做储备的“话本”。民间段子正因为有这种效果,成为大众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且有效的话语,在黄段子灰段子的讲述和哄笑声中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权贵或彻底低俗的情境中人们感觉到某种同一性,此时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得意失意,“人人回归自我”,获得一种“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民间段子的盛行就是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对权力的抵抗和对权力符号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会同时夹杂无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说明问题: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2012之前:我们用奶粉毁掉00后,考试毁掉90后,房价毁掉80后,失业毁掉70后,城管毁掉60后,下岗毁掉50后,拆迁毁掉40后,医改毁掉30后。(此处的“2012”源于美国2009年上映的灾难片《2012:世界末日》,引者注)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类段子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概括也许不够准确,甚至充满偏激,但说明了这些年人们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的同时,环顾四周,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势使人们对世界不断陌生化,连怀旧的时间和对象都找不到,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官员的腐败,社会诚信的缺乏,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热潮……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在餐桌酒酣之际,在同辈聚会之时,借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狂欢,为这些充满不满、忧惧、受挫的心灵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继续沉重的生活。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描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许把“宗教”改为“段子”亦有相通之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段子那么盛行的深层根源。二、规训与惩罚随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实上给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不少冲击,甚至给所谓“正统”道德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多来自文化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方意见代表带来了恐慌。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曾经出现过密集地讨伐黄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见认为,黄段子灰段子格调低下、庸俗无聊,甚至认为黄段子激发性欲导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黄段子定性为一种性骚扰等等。河北省深泽县纪委在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传播黄段子的文件中说,(黄段子)“低俗信息不仅毒害人的心灵、涣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蚀道德意识,已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甚至是腐败的温床”。2005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文件,严禁公务员在各种场合讲黄段子和传播黄段子,否则将被“处理”。2009年,河北深泽县竟然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6万余党员参与学习领会该县纪委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使用手机留存和传播“黄段子”的红头文件。报道称如经举报查实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和单位领导连带责任。 2006年,网络和各地方报纸上频频出现《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为标题的新闻,新闻说2006年3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其内容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73种增加至110多种,许多过去管理无凭、处罚无据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新法第42条明确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据说各地方政府又根据这条法规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细则,一时间“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讹传讹地得出 “传播黄段子是犯罪行为”、“发黄段子短信将被拘留”等说法,尽管有夸大和不实的成分,但多少也体现了官方的意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检查自己的手机,删掉手机上存留的涉嫌“黄”的短信。尽管后来未见有坐实案例报导,但“传播黄段子违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里,体现出统治者调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自发的民间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黄段子进行了一定成效的监管和遏制,采用的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手段。但由于这种监管和权力意志的过于强悍和独断,随之也引发了诸多在学理、法律层面的质疑与讨论。比如,如何确定黄段子与性骚扰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如何界定黄段子的标准等。有人提出这种监管会不会导致公权的滥用,如河北深泽县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是不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滥用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靠简单粗暴的禁止与惩罚似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给文化领导者出了一个难题。在这种局势下,红段子进入了文化领导者的视野,并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开创红段子短信大赛,大赛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抵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些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黄段子灰段子的负面影响而举办的。此后红段子短信大赛连续举办五年,全国多个省市都学习广东模式举办类似的红段子大赛。2010年2月11日,代表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以“手机红段子引领和谐文化”为题进行正式报道,将红段子命名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短信文化形式”。 2010年10月,《光明日报》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谁不说咱家乡好”的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红段子由个别的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表达升格到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高度,并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接管与推行。一时间红段子红遍大江南北,2009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该书在理论的高度给红段子进行了价值定位:“红段子掀起中国的红色新文化运动,”“我们应重拾汉唐盛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巨大影响力,创造网络时代风雷激荡的文化历史”。该书开宗明义“用‘红段子’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先破后立,意在‘主流话语权’”。 据此,红段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完成华丽转型。与民间自发的段子不同,红段子完全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诱导和规范(有奖征文比赛等方式)下进行的、并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传播的“仿”民间段子的话语形式。其话语方式是利用民间段子的表现形式,置换民间段子的内容,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确的政治观念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纳入其中,以达到“弘扬正气、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目的。红段子内容上多是励志短句、哲理箴言、节庆祝福之类,审美上尽量引导创造者(编写者)将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立场与人民大众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具有审美普遍性同时又具备党性原则的“红色新文化”。“‘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占领主流文化阵地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规训,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普遍运作原则。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询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具有一种“将个体询换为主体”的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一个或多个的观念赋予“主体”,这些关于“主体”的想象使主体直面个体,以个体的名义向赋予他想象性主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通过我称之为构建(interpellation)或呼叫(hailing)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或其他人)呼叫:‘喂!喂!’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recruits)主体(招募所有的个人)或者把个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体(改造所有的个人)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acts)或‘产生作用’(functions)的。” 红段子以充满人生哲理的劝世箴言、积极振奋的人生态度、温馨真诚的祝福话语共同构筑起一个关于和谐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不满与缺憾,引导民众参与并共同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前相互认可,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红段子要做的就是设法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使人们在关于温馨、美好、幸福、和谐的社会图景中达成共同的想象,并试图激发人民大众对生活对社会产生共同的向往和渴望进而实现审美交流,最终通过红段子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情感表达与当下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达成社会的和谐。在这里,红段子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们精神的领袖、生活的导师、知心的朋友、贴心的亲人……如: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则是一朵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湛蓝的天空,那么失意则是一片漂浮的白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大忧为国小忧为家。常怀博爱仁厚之心,待人诚挚待事圆滑。勿以己悲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处之。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摘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尊酒,但愿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试想,你的生活中经常被这些话语包围,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中,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幸福健康,让你感觉生活的美满,让你觉得人生值得一过,让你珍惜现在,安于现状……其实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幻象。在这里,红段子充当一种“新文艺”,它是一种既有哲理意味且同时饱含温情的情感性话语,具有一种审美的效果。根据文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识形态属性,马歇雷说,“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在某种意义上,审美的效果和意识形态的效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关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说:“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它是人类团结的源泉。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放任个体陷于孤独的自律,那就只有通过这种想象性的交流或相互适应的同一性,个体才能被紧密地结合起来。” 又说:“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以文艺审美的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情感性话语与政治意识等等之间产生和谐。红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黄段子灰段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伊格尔顿分析了审美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审美艺术品总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精神和感觉和谐地相互联起来”。基于美学的这个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效果:“主体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过教育和以实践为中介的欲望的理性教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导权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建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了情感在文化(政治)领导权争夺中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会内聚力能够形成的根源,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话语,从它产生之时就作为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强权的压迫,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这就是红段子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运作机制,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转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温和规训,应该说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呢?按主流媒体的报道,红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如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数度南下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行跟踪调研,并根据‘红段子’活动的实践与经验……历时一年”编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性成果《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再诸如《“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等标题可见一斑。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红段子的“伪”民间性,使得它在根源上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与民间段子的自发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实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和传播的红段子,则缺乏这些特质。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红段子情感苍白内容空洞,劝世箴言变成意识形态的说教,生活哲理成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很多红段子与流行歌曲唱的“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天天都是好日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其机械复制和没有明确对象的无限“群发”的特点,使红段子失去了真正的经验传达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应该离老百姓最为亲近的“真情祝福”的红段子来看,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性和针对性,在以短信“群发”的传送下变成一种空洞的祝福形式。如有一名学生在中秋节给我群发一个祝福:窗前明月光,秋风满庭芳;疑是地上霜,忽闻桂花香;举头望明月,即将中秋节;低头思念长,于是祝福忙:中秋将至,愿你月发幸福,月发健康!而另一名学生发这么一个祝福短信:“中秋将至,学生某某祝吴老师中秋快乐。”就表达形式而言,前者似乎显得更有审美性,更有情怀和诗意,更温馨美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成品,也许根本就没有祝福者个人的真正情感在里面,只是顺手的一个转发,而且我还知道他同时还发给了很多人,甚至在一天之内我会收到若干个与此一模一样的祝福信息。对比之下,后者的祝福尽管简单甚至简陋,但我知道这是指向我的、祝福者亲自输入的专属的一个情感表达,因此个人觉得后者更显得真诚一些。红段子如果没能具备民间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质,哪怕内容再健康、正确、积极、再“高大上”,也难以深入人心,最终只流于空泛,遭遇尴尬。三、僭越与和解作为主流文化领导者,面对无绪杂乱的民间俗文化形式的泛滥,要重树价值规范、扭转文艺方向,对低俗有害的自发文化进行抵制和引导,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抵抗的时候能想到文艺具有《毛诗序》里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抗衡、收编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夺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可取的。但官方意识形态在收编、整合和引导的时候应该遵循文艺的规律和原则。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而不考虑文艺自身的特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与打压,这一点值得商榷。从理论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的收编和规训,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损害。文化研究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文人对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改编、历代统治者对文艺的干涉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改造。户晓辉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或民俗”与作家收集整理出版的“文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差异之大达十多项,“但是,其中的差别还不止这些。一旦民间艺术被中产阶级作家和出版家挪用并且被变成以大众为中介的印刷形式,它就承受了剧烈的变化……它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角度就被泯没、丢失或置换了”。 同样道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段子的打压与规训,以民间段子形式置换出来的所谓红段子在很大程度上异质化了,最终红段子变成一种矛盾体。从文艺规律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僭越。就如当年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它以收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汇总和改编了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歌谣和打油诗。这种来自民间的歌谣按理说是最能够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心声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曾大量引用农民起义时期的各种歌谣和童谣来作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证据。但《红旗歌谣》在农业歉收和政策失误之下的中国民间却有“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等诸如此类的描述。这次活动显然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话语的一次现代的模仿,是以郭沫若和周扬为代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采风活动,现在看来是一次权力僭越的在文艺上收获不大的文化生产的浮夸行为。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红段子最终的效果;红段子没有推行之前,民间自发的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真的如文化领导者所说的那样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或性犯罪吗?这些民间段子真的对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构成威胁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谓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有话语权者对无话语权者的判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这个不赘述。至于说黄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这个则可以辩证来看。色情的文艺主要是激发人的性欲,指在文艺中对性交的细致描述、性器状况的描写以及性感受的铺排,但黄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作为符号或由头引发嘲讽或嘲笑的。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权力压抑的能量获得释放,既消解了权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说黄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发人的性欲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实践中很少有围听黄段子者性欲盎然的情况。如下面两个典型的黄段子:男知妻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听后气极说:“咱们也上床报复他俩!”事毕领导妻又说:“我还气,再报复一次!”一连三次,男跪倒趴下告饶:“求求你了,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一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检验结果出来了。但医院居然拿错了报告,误拿了孕妇的报告,检验结果怀孕了。男子看过报告后,迅速走到老婆面前,扇了老婆一个耳光!男子对老婆骂道:“我说我要在上面,你不干!偏偏你要在上面,这下,我怀孕了。” 以上这几个段子尽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并不是性本身,没有刻意赋予更多的性暗示,听众基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黄段子的叙事中,能指与所指往往是断裂的。另外,民间段子对官方意识形态有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冲动,但若说民间段子的流行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和实际威胁,这是不确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同时也很隐秘的自我修复和同化功能,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对另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抵抗,同时在抵抗的幻象式快感中就消解了对前者的实际反抗。亨利·吉罗等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中分析说:“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前面关于民间段子与红段子的分析也说明,他们的机制都是制造乌托邦,在最终的运作效果上基本是殊途同归的。最终来看,民间段子并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实质性的颠覆或占领,某种意义上还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固性。阿多诺就曾把大众文化当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稳固剂,是一种“社会水泥”。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间段子的娱乐消闲方式缓解了大众对社会的紧张感,反而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国在大众文化繁荣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是在“重视、支持、引导”的口号下对大众俗文化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间段子与红段子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层面上尽管方向不同,但最终被整体性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解与吸收,则是一样的,在某种高度上,他们达到了和解。所以,这次文化领导者对民间段子的恐慌与严厉,并以红段子来相抗衡争夺主流文化领导权,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也许在这次红段子的推导中,不乏权力的僭越的表现,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量与比拼,某县的480多场会议等,多是出于其他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寻租行为。另外,在红段子推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商业运作跟制度权力形成了合谋。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人为地制造对抗,意欲以强制性国家机器对黄段子讲述、传播进行惩罚,并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倡、领导、布置、审查、验收、整理作为文化生产方式的“红色新文化运动”也许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但是否也因此干涉或削弱了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呢?结语目前,一度曾经令有关部门担心会“黄祸”泛滥、世风败坏的黄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沉寂,红段子也由于它内在的空虚而又过于密集频繁地侵入人们的意识世界而被人故意地无视或无意地反感,也逐渐走向节制和沉默。综观这两类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博弈。我们还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抵抗和争夺,最终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归。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意识形态其实是人同现实联系的中介,是人对世界的感觉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表征,人们通过它,借以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启蒙与解放都来源于意识形态这个“表现系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这个“表现系统”进行分析,揭示它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深入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多了一种可能。[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吴高泉,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辑:若水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独立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摘要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关键词 黄段子;灰段子;红段子;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作为俗文化中最为贴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间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来以旺盛的生命力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近些年,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互联网的发达以及新兴便捷媒介手机、ipad等的勃兴,段子文化成为一种蔚为奇观的大众文化现象。然学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与政治等敏感话题而研究的不多,隐隐体现出一种不敢、不愿或不屑的心态。而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红段子”的言说,学界则普遍表现相对踊跃。较早从学术角度论及段子的是2008年《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上的一篇《段子管窥》,该文对段子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广义的段子,指的是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赏的、简短自足的或长篇中可独立出来的短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话、小品,也可以指戏剧中的唱段……狭义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尤其指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幽默类的故事、笑话、脱口秀、顺口溜等……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亦采用这个界定,所论的段子属于以上所说的狭义的段子。将近年流行的各类段子以颜色分为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等,既体现了人们对段子内容的区分也体现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简言之,黄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为话题及取笑对象的段子,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灰段子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抨击时弊或表达现实无奈的自嘲的段子,体现出一种灰色的心态或黑色幽默的特点;红段子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制作、传播的一种代表健康社会心理、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短信息文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与民间自发流传的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民众的精神空间,打击黄段子灰段子所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在段子的喧哗世界里,很典型地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和博弈。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这两大类具有对抗性质的段子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无意识和意识形态企图。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以上溯到20世纪文学批评中以文学的话语方式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这一传统摒弃了过去文学批评以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意图的臆测、抽象的美学特征、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而转向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进行“症候式”的阅读,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话语分析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多数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人民“真实”的情感表达,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对统治权力的某种抵抗,大众文化是差异文化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什么是大众文化,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按照这个界定,中国内地近年流行的民间段子完全具备大众文化的特点,而且在表达的内容、创作的方式、传播的途径、意识形态的诉求等方面,比一般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如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更具有“大众”的身份和特点。因此,我们对当前大众文化中的这种代表形式——“段子”——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性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一、抵抗与消解要理解民间段子所表达的平民意识形态诉求,最好的方式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间段子(本文主要指黄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何以在中国内地盛行的原因。关于盛行原因,目前学界相关说法一般都比较务实,如《段子管窥》认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餐文化的消费;具有高度的娱乐性。《“黄段子”为何流行》认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绪放松的快乐,三是交友的需要。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娱乐、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艺术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与今天的段子内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艺现象,都可以说也具有以上所说的功用。明末冯梦龙《挂枝儿》《山歌》和《广笑府》里收集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行“歌曲”和笑话有很多就属于今天理解的黄段子和灰段子。仅举几例:牙刷儿,身材短,刚刚五六寸,穿一领香喷喷绿背心。一条骨子儿生成的硬,短鬅松一搭毛儿黑,光油油好一个下半身。专与那唇齿相交也,(每日里)擦一阵儿爽快得很。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根头。姐道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铁线身粗慢慢里抽。姐儿生来像花开,花心未动等春来。囫囵囵两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里含羞夜里开。一僧读“齋”字,尼认是“齊”字,因而相争。一人断之曰:“上头是一样的,但是下头略有些差”。或问好色者曰:“世间何事最乐?”答曰:“行房最乐。”又问:“既行房后,还有甚乐?”沉吟曰:“除是再行。”官值暑日,欲寻避暑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凉。一皂隶曰:“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问其故,答曰:“此地有天无日头。”前面几则或隐或显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段子,其中第5则在当下被改成湖南或四川方言再次在民间流行(只是把“行房”改为“做爱”,最后一句改为“再做一次”)。第6则对有权者的讥讽则类似于今天的灰段子。如果单从民间文艺的一般功用角度来分析流行原因的话,似乎无法解释民间段子为什么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一层的追问,即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大量需要段子来消遣、娱乐、宣泄、交流?冯梦龙收集的这些大量涉及私情、欲望的民间“段子”在当时的盛行原因或可资参考。涉性的民间原生态的“段子”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只是过于“俚俗”“粗鄙”而不被文人收录和记载,它只能潜流于生活的当下,由于没有资料记载,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现冯梦龙这样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段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类似“段子”的大量流传。明末市民社会发达,民众的娱乐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于引起文人的关注,甚至介入收集、仿制和传播的行列;另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与当时新兴印刷技术的大众化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明显地强调其传播的“大众”、“消费”的媒介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民间段子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发达产生了其广泛的受众,最为关键的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明清时期的刊刻造纸技术对俗文化的推动一样,近年国内民间段子的盛行与新兴的互联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手机短信平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电子传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广,使民众广泛参与、广泛传播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传媒交互平台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欢迎,客观上引导和鼓励了人们进行碎片式(“段”)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的审美体验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的红段子也正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平台得以顺利有效施行的。第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涉及民间段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所承载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识形态诉求。尽管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但民众对转型期内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感受深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转折点在近一百年来并不多,历数起来大致是“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效应上近年表现逐渐明显。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商业浪潮和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切身体验,并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普遍的表达。与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相比,世纪之交前后的这20来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现代性体验。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很像西方社会之前经历的那种转型,只是我们在时间上滞后了而已。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些年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但有些地方用来形容中国社会近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亦有相似之处。如商品经济浪潮的推拥裹挟、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等都给人带来普遍的变动感,尤其是在这个急剧转型中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似未成熟——这从近年来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这一点给人带来很多的迷惘和焦虑。人们处在土地征用、拆迁、城市化等空间的迅速转变当中,处在拼命追赶“与时俱进”的各种不确定的事物变化当中,处在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失范诚信缺乏的危险境地当中,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浮躁和戾气当中……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总结回顾中,“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反观自身的时候,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种短平快且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俗文化形式——民间段子——在新兴电子传媒的推动下蓬勃兴起,人们在这些充满戏谑、狂欢、讽刺、自嘲的话语中深获共鸣。由于民间段子结构的松散性、主题的随意性、艺术的通俗性,几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创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衍化繁殖,体现出集体的智慧与趣味,再通过能够迅速传播的公共传播手段,使得人们同声相应,手、口、耳相传,最终形成一股全民狂欢的风气。在这种文化狂欢的背后,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无意识和平民意识形态的诉求,包含有一种无声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对权力压抑的消解。这可以从民间段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从内容上看,黄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与性器,带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话以及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的嘲讽。性与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属于禁忌的话题,禁忌的内容、禁忌的惩戒,意味在此之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力和制度权力。冲破这些禁忌,意味着一种抵抗和解放,并因此获得某种匿名的快感。这一点很像西方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的摇滚乐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摇滚乐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摇滚乐却得到不少赞赏,甚至文化研究的论者还把摇滚乐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摇滚乐的粗鄙、炫耀式的“堕落”,狂欢化和快感原则,甚至它的命运和遭遇,都跟黄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摇滚文化只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和肆无忌惮的“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话,中国近年盛行的民间段子则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狂欢文化。约翰·费斯克在论及大众文化的资本时曾指出:“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按照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权力给人的快感是双向的,“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无权的大众阶层很多时候喜欢通过低俗、鄙俗甚至淫秽的黄段子对道德话语权力进行挑战,以粗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带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意味。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使黄段子的讲述者与听众体会一种充满“机智”“巧妙”的创造性反应,获得“狡黠”“恶毒”的快感。如:一男子到医院做非典检查,护士取针刺手指为其验血,因一时没棉花,情急中护士赶紧将其手指含入口中。男子痴迷半晌后款款的说:我想再做个尿检。乡长穿着短裤作报告,讲到激动时把一只脚抬放在椅子上,小弟弟露了出来,会场一片哗然,他以为大家不耐烦,就大声说:这只是个头,后面还长着呢!以上几个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种符号,它不是叙事意欲突出的内容,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使叙事的氛围变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话语权力的整体沦陷中人们觉得亲密无间,有一种集体抵抗同一战线的快感。又如:政府做完工程却省下一大笔钱,于是众人开会举手表决。是把这笔钱拿来改造中小学还是改善监狱环境。会议分成两派,众人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老常委一语定乾坤:“你们这班子人这辈子还有机会上中小学么?”顿时众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决定改善监狱环境……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辨别真正成功人士: 1.没有名片;2.自己不开车;3.衣服没logo;4.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5.每天午睡;6.经常在郊区活动;7.包里现金很少……旁边一位农民兴奋地打断:“这种人,我们村全是!”以上两例是灰段子的常用叙事模式,用强烈的反差造成反讽,对权力符号的揶揄和解构,在听众的哄堂大笑中神圣、庄严的东西轰然倒塌。无权无势无财的大众在一无所有中往往只能通过灰段子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讽刺以及对权力符号的消解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嘲弄腐败官员、为富不仁的富贵者(他们一般被符号化为“贪官”“煤矿老板”“暴发户”等)的愚昧、无能、丑陋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体会一种对原权力进行嘲弄的权力,产生一种“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并“证实自身”,产生一种阶级认同,获得慰藉和温暖。这种精神胜利快感的表现形式在于民间段子独特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中激赏拉伯雷在笑谑民间文学收集和创作上的成就,他说:“人们一般提及,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性的地位。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 因此,拉伯雷被不少人指责,但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的、“鄙俗化”的风格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及民间获得解放的力量。而广场言语和狂欢化是民间笑谑文学的话语特点,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日常的、亦即非狂欢的生活中,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在这里)异化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群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 在论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阐发道:“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这种笑声是个矛盾体,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解放性)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现象的雏形——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段子所具有的广场言语和狂欢化的特点,决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种纯粹提供给人阅读的文本,其效果往往需要话语的讲述来呈现,具有一种“在场”性和“表演”性。“在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段子的讲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会上、旅行团的车上,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如网络论坛、QQ群、微信朋友圈等),起到一种交往和聚众狂欢的效果。“表演”性表现在讲述的时候注重模仿(行动、语气、口音等)、注重互动和即兴发挥。尽管很多民间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传播,但也只是为了扩散,作为聚众时候讲述做储备的“话本”。民间段子正因为有这种效果,成为大众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且有效的话语,在黄段子灰段子的讲述和哄笑声中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权贵或彻底低俗的情境中人们感觉到某种同一性,此时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得意失意,“人人回归自我”,获得一种“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民间段子的盛行就是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对权力的抵抗和对权力符号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会同时夹杂无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说明问题: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2012之前:我们用奶粉毁掉00后,考试毁掉90后,房价毁掉80后,失业毁掉70后,城管毁掉60后,下岗毁掉50后,拆迁毁掉40后,医改毁掉30后。(此处的“2012”源于美国2009年上映的灾难片《2012:世界末日》,引者注)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类段子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概括也许不够准确,甚至充满偏激,但说明了这些年人们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的同时,环顾四周,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势使人们对世界不断陌生化,连怀旧的时间和对象都找不到,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官员的腐败,社会诚信的缺乏,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热潮……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在餐桌酒酣之际,在同辈聚会之时,借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狂欢,为这些充满不满、忧惧、受挫的心灵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继续沉重的生活。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描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许把“宗教”改为“段子”亦有相通之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段子那么盛行的深层根源。二、规训与惩罚随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实上给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不少冲击,甚至给所谓“正统”道德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多来自文化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方意见代表带来了恐慌。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曾经出现过密集地讨伐黄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见认为,黄段子灰段子格调低下、庸俗无聊,甚至认为黄段子激发性欲导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黄段子定性为一种性骚扰等等。河北省深泽县纪委在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传播黄段子的文件中说,(黄段子)“低俗信息不仅毒害人的心灵、涣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蚀道德意识,已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甚至是腐败的温床”。2005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文件,严禁公务员在各种场合讲黄段子和传播黄段子,否则将被“处理”。2009年,河北深泽县竟然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6万余党员参与学习领会该县纪委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使用手机留存和传播“黄段子”的红头文件。报道称如经举报查实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和单位领导连带责任。 2006年,网络和各地方报纸上频频出现《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为标题的新闻,新闻说2006年3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其内容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73种增加至110多种,许多过去管理无凭、处罚无据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新法第42条明确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据说各地方政府又根据这条法规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细则,一时间“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讹传讹地得出 “传播黄段子是犯罪行为”、“发黄段子短信将被拘留”等说法,尽管有夸大和不实的成分,但多少也体现了官方的意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检查自己的手机,删掉手机上存留的涉嫌“黄”的短信。尽管后来未见有坐实案例报导,但“传播黄段子违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里,体现出统治者调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自发的民间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黄段子进行了一定成效的监管和遏制,采用的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手段。但由于这种监管和权力意志的过于强悍和独断,随之也引发了诸多在学理、法律层面的质疑与讨论。比如,如何确定黄段子与性骚扰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如何界定黄段子的标准等。有人提出这种监管会不会导致公权的滥用,如河北深泽县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是不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滥用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靠简单粗暴的禁止与惩罚似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给文化领导者出了一个难题。在这种局势下,红段子进入了文化领导者的视野,并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开创红段子短信大赛,大赛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抵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些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黄段子灰段子的负面影响而举办的。此后红段子短信大赛连续举办五年,全国多个省市都学习广东模式举办类似的红段子大赛。2010年2月11日,代表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以“手机红段子引领和谐文化”为题进行正式报道,将红段子命名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短信文化形式”。 2010年10月,《光明日报》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谁不说咱家乡好”的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红段子由个别的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表达升格到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高度,并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接管与推行。一时间红段子红遍大江南北,2009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该书在理论的高度给红段子进行了价值定位:“红段子掀起中国的红色新文化运动,”“我们应重拾汉唐盛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巨大影响力,创造网络时代风雷激荡的文化历史”。该书开宗明义“用‘红段子’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先破后立,意在‘主流话语权’”。 据此,红段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完成华丽转型。与民间自发的段子不同,红段子完全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诱导和规范(有奖征文比赛等方式)下进行的、并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传播的“仿”民间段子的话语形式。其话语方式是利用民间段子的表现形式,置换民间段子的内容,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确的政治观念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纳入其中,以达到“弘扬正气、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目的。红段子内容上多是励志短句、哲理箴言、节庆祝福之类,审美上尽量引导创造者(编写者)将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立场与人民大众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具有审美普遍性同时又具备党性原则的“红色新文化”。“‘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占领主流文化阵地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规训,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普遍运作原则。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询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具有一种“将个体询换为主体”的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一个或多个的观念赋予“主体”,这些关于“主体”的想象使主体直面个体,以个体的名义向赋予他想象性主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通过我称之为构建(interpellation)或呼叫(hailing)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或其他人)呼叫:‘喂!喂!’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recruits)主体(招募所有的个人)或者把个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体(改造所有的个人)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acts)或‘产生作用’(functions)的。” 红段子以充满人生哲理的劝世箴言、积极振奋的人生态度、温馨真诚的祝福话语共同构筑起一个关于和谐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不满与缺憾,引导民众参与并共同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前相互认可,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红段子要做的就是设法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使人们在关于温馨、美好、幸福、和谐的社会图景中达成共同的想象,并试图激发人民大众对生活对社会产生共同的向往和渴望进而实现审美交流,最终通过红段子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情感表达与当下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达成社会的和谐。在这里,红段子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们精神的领袖、生活的导师、知心的朋友、贴心的亲人……如: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则是一朵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湛蓝的天空,那么失意则是一片漂浮的白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大忧为国小忧为家。常怀博爱仁厚之心,待人诚挚待事圆滑。勿以己悲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处之。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摘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尊酒,但愿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试想,你的生活中经常被这些话语包围,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中,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幸福健康,让你感觉生活的美满,让你觉得人生值得一过,让你珍惜现在,安于现状……其实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幻象。在这里,红段子充当一种“新文艺”,它是一种既有哲理意味且同时饱含温情的情感性话语,具有一种审美的效果。根据文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识形态属性,马歇雷说,“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在某种意义上,审美的效果和意识形态的效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关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说:“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它是人类团结的源泉。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放任个体陷于孤独的自律,那就只有通过这种想象性的交流或相互适应的同一性,个体才能被紧密地结合起来。” 又说:“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以文艺审美的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情感性话语与政治意识等等之间产生和谐。红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黄段子灰段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伊格尔顿分析了审美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审美艺术品总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精神和感觉和谐地相互联起来”。基于美学的这个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效果:“主体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过教育和以实践为中介的欲望的理性教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导权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建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了情感在文化(政治)领导权争夺中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会内聚力能够形成的根源,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话语,从它产生之时就作为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强权的压迫,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这就是红段子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运作机制,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转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温和规训,应该说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呢?按主流媒体的报道,红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如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数度南下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行跟踪调研,并根据‘红段子’活动的实践与经验……历时一年”编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性成果《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再诸如《“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等标题可见一斑。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红段子的“伪”民间性,使得它在根源上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与民间段子的自发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实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和传播的红段子,则缺乏这些特质。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红段子情感苍白内容空洞,劝世箴言变成意识形态的说教,生活哲理成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很多红段子与流行歌曲唱的“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天天都是好日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其机械复制和没有明确对象的无限“群发”的特点,使红段子失去了真正的经验传达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应该离老百姓最为亲近的“真情祝福”的红段子来看,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性和针对性,在以短信“群发”的传送下变成一种空洞的祝福形式。如有一名学生在中秋节给我群发一个祝福:窗前明月光,秋风满庭芳;疑是地上霜,忽闻桂花香;举头望明月,即将中秋节;低头思念长,于是祝福忙:中秋将至,愿你月发幸福,月发健康!而另一名学生发这么一个祝福短信:“中秋将至,学生某某祝吴老师中秋快乐。”就表达形式而言,前者似乎显得更有审美性,更有情怀和诗意,更温馨美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成品,也许根本就没有祝福者个人的真正情感在里面,只是顺手的一个转发,而且我还知道他同时还发给了很多人,甚至在一天之内我会收到若干个与此一模一样的祝福信息。对比之下,后者的祝福尽管简单甚至简陋,但我知道这是指向我的、祝福者亲自输入的专属的一个情感表达,因此个人觉得后者更显得真诚一些。红段子如果没能具备民间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质,哪怕内容再健康、正确、积极、再“高大上”,也难以深入人心,最终只流于空泛,遭遇尴尬。三、僭越与和解作为主流文化领导者,面对无绪杂乱的民间俗文化形式的泛滥,要重树价值规范、扭转文艺方向,对低俗有害的自发文化进行抵制和引导,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抵抗的时候能想到文艺具有《毛诗序》里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抗衡、收编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夺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可取的。但官方意识形态在收编、整合和引导的时候应该遵循文艺的规律和原则。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而不考虑文艺自身的特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与打压,这一点值得商榷。从理论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的收编和规训,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损害。文化研究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文人对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改编、历代统治者对文艺的干涉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改造。户晓辉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或民俗”与作家收集整理出版的“文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差异之大达十多项,“但是,其中的差别还不止这些。一旦民间艺术被中产阶级作家和出版家挪用并且被变成以大众为中介的印刷形式,它就承受了剧烈的变化……它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角度就被泯没、丢失或置换了”。 同样道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段子的打压与规训,以民间段子形式置换出来的所谓红段子在很大程度上异质化了,最终红段子变成一种矛盾体。从文艺规律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僭越。就如当年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它以收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汇总和改编了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歌谣和打油诗。这种来自民间的歌谣按理说是最能够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心声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曾大量引用农民起义时期的各种歌谣和童谣来作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证据。但《红旗歌谣》在农业歉收和政策失误之下的中国民间却有“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等诸如此类的描述。这次活动显然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话语的一次现代的模仿,是以郭沫若和周扬为代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采风活动,现在看来是一次权力僭越的在文艺上收获不大的文化生产的浮夸行为。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红段子最终的效果;红段子没有推行之前,民间自发的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真的如文化领导者所说的那样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或性犯罪吗?这些民间段子真的对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构成威胁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谓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有话语权者对无话语权者的判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这个不赘述。至于说黄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这个则可以辩证来看。色情的文艺主要是激发人的性欲,指在文艺中对性交的细致描述、性器状况的描写以及性感受的铺排,但黄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作为符号或由头引发嘲讽或嘲笑的。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权力压抑的能量获得释放,既消解了权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说黄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发人的性欲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实践中很少有围听黄段子者性欲盎然的情况。如下面两个典型的黄段子:男知妻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听后气极说:“咱们也上床报复他俩!”事毕领导妻又说:“我还气,再报复一次!”一连三次,男跪倒趴下告饶:“求求你了,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一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检验结果出来了。但医院居然拿错了报告,误拿了孕妇的报告,检验结果怀孕了。男子看过报告后,迅速走到老婆面前,扇了老婆一个耳光!男子对老婆骂道:“我说我要在上面,你不干!偏偏你要在上面,这下,我怀孕了。” 以上这几个段子尽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并不是性本身,没有刻意赋予更多的性暗示,听众基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黄段子的叙事中,能指与所指往往是断裂的。另外,民间段子对官方意识形态有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冲动,但若说民间段子的流行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和实际威胁,这是不确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同时也很隐秘的自我修复和同化功能,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对另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抵抗,同时在抵抗的幻象式快感中就消解了对前者的实际反抗。亨利·吉罗等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中分析说:“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前面关于民间段子与红段子的分析也说明,他们的机制都是制造乌托邦,在最终的运作效果上基本是殊途同归的。最终来看,民间段子并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实质性的颠覆或占领,某种意义上还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固性。阿多诺就曾把大众文化当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稳固剂,是一种“社会水泥”。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间段子的娱乐消闲方式缓解了大众对社会的紧张感,反而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国在大众文化繁荣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是在“重视、支持、引导”的口号下对大众俗文化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间段子与红段子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层面上尽管方向不同,但最终被整体性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解与吸收,则是一样的,在某种高度上,他们达到了和解。所以,这次文化领导者对民间段子的恐慌与严厉,并以红段子来相抗衡争夺主流文化领导权,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也许在这次红段子的推导中,不乏权力的僭越的表现,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量与比拼,某县的480多场会议等,多是出于其他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寻租行为。另外,在红段子推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商业运作跟制度权力形成了合谋。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人为地制造对抗,意欲以强制性国家机器对黄段子讲述、传播进行惩罚,并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倡、领导、布置、审查、验收、整理作为文化生产方式的“红色新文化运动”也许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但是否也因此干涉或削弱了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呢?结语目前,一度曾经令有关部门担心会“黄祸”泛滥、世风败坏的黄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沉寂,红段子也由于它内在的空虚而又过于密集频繁地侵入人们的意识世界而被人故意地无视或无意地反感,也逐渐走向节制和沉默。综观这两类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博弈。我们还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抵抗和争夺,最终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归。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意识形态其实是人同现实联系的中介,是人对世界的感觉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表征,人们通过它,借以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启蒙与解放都来源于意识形态这个“表现系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这个“表现系统”进行分析,揭示它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深入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多了一种可能。[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吴高泉,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辑:若水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独立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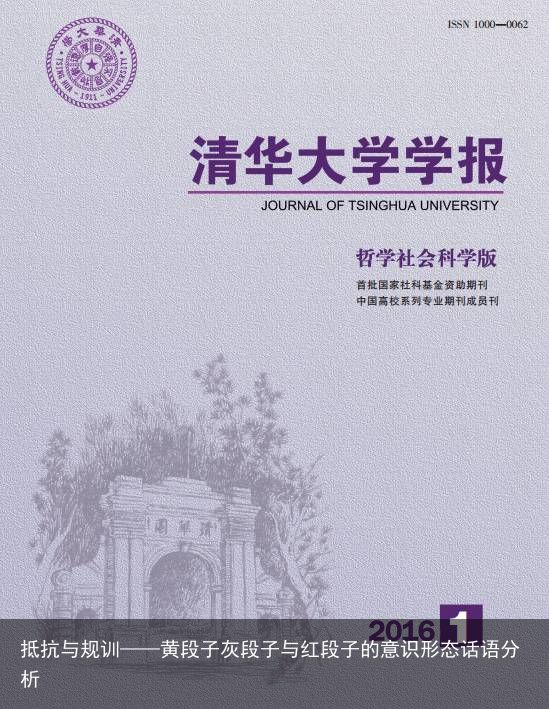 摘要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关键词 黄段子;灰段子;红段子;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作为俗文化中最为贴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间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来以旺盛的生命力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近些年,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互联网的发达以及新兴便捷媒介手机、ipad等的勃兴,段子文化成为一种蔚为奇观的大众文化现象。然学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与政治等敏感话题而研究的不多,隐隐体现出一种不敢、不愿或不屑的心态。而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红段子”的言说,学界则普遍表现相对踊跃。较早从学术角度论及段子的是2008年《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上的一篇《段子管窥》,该文对段子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广义的段子,指的是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赏的、简短自足的或长篇中可独立出来的短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话、小品,也可以指戏剧中的唱段……狭义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尤其指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幽默类的故事、笑话、脱口秀、顺口溜等……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亦采用这个界定,所论的段子属于以上所说的狭义的段子。将近年流行的各类段子以颜色分为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等,既体现了人们对段子内容的区分也体现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简言之,黄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为话题及取笑对象的段子,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灰段子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抨击时弊或表达现实无奈的自嘲的段子,体现出一种灰色的心态或黑色幽默的特点;红段子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制作、传播的一种代表健康社会心理、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短信息文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与民间自发流传的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民众的精神空间,打击黄段子灰段子所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在段子的喧哗世界里,很典型地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和博弈。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这两大类具有对抗性质的段子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无意识和意识形态企图。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以上溯到20世纪文学批评中以文学的话语方式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这一传统摒弃了过去文学批评以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意图的臆测、抽象的美学特征、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而转向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进行“症候式”的阅读,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话语分析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多数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人民“真实”的情感表达,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对统治权力的某种抵抗,大众文化是差异文化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什么是大众文化,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按照这个界定,中国内地近年流行的民间段子完全具备大众文化的特点,而且在表达的内容、创作的方式、传播的途径、意识形态的诉求等方面,比一般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如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更具有“大众”的身份和特点。因此,我们对当前大众文化中的这种代表形式——“段子”——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性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一、抵抗与消解要理解民间段子所表达的平民意识形态诉求,最好的方式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间段子(本文主要指黄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何以在中国内地盛行的原因。关于盛行原因,目前学界相关说法一般都比较务实,如《段子管窥》认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餐文化的消费;具有高度的娱乐性。《“黄段子”为何流行》认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绪放松的快乐,三是交友的需要。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娱乐、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艺术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与今天的段子内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艺现象,都可以说也具有以上所说的功用。明末冯梦龙《挂枝儿》《山歌》和《广笑府》里收集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行“歌曲”和笑话有很多就属于今天理解的黄段子和灰段子。仅举几例:牙刷儿,身材短,刚刚五六寸,穿一领香喷喷绿背心。一条骨子儿生成的硬,短鬅松一搭毛儿黑,光油油好一个下半身。专与那唇齿相交也,(每日里)擦一阵儿爽快得很。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根头。姐道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铁线身粗慢慢里抽。姐儿生来像花开,花心未动等春来。囫囵囵两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里含羞夜里开。一僧读“齋”字,尼认是“齊”字,因而相争。一人断之曰:“上头是一样的,但是下头略有些差”。或问好色者曰:“世间何事最乐?”答曰:“行房最乐。”又问:“既行房后,还有甚乐?”沉吟曰:“除是再行。”官值暑日,欲寻避暑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凉。一皂隶曰:“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问其故,答曰:“此地有天无日头。”前面几则或隐或显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段子,其中第5则在当下被改成湖南或四川方言再次在民间流行(只是把“行房”改为“做爱”,最后一句改为“再做一次”)。第6则对有权者的讥讽则类似于今天的灰段子。如果单从民间文艺的一般功用角度来分析流行原因的话,似乎无法解释民间段子为什么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一层的追问,即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大量需要段子来消遣、娱乐、宣泄、交流?冯梦龙收集的这些大量涉及私情、欲望的民间“段子”在当时的盛行原因或可资参考。涉性的民间原生态的“段子”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只是过于“俚俗”“粗鄙”而不被文人收录和记载,它只能潜流于生活的当下,由于没有资料记载,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现冯梦龙这样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段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类似“段子”的大量流传。明末市民社会发达,民众的娱乐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于引起文人的关注,甚至介入收集、仿制和传播的行列;另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与当时新兴印刷技术的大众化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明显地强调其传播的“大众”、“消费”的媒介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民间段子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发达产生了其广泛的受众,最为关键的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明清时期的刊刻造纸技术对俗文化的推动一样,近年国内民间段子的盛行与新兴的互联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手机短信平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电子传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广,使民众广泛参与、广泛传播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传媒交互平台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欢迎,客观上引导和鼓励了人们进行碎片式(“段”)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的审美体验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的红段子也正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平台得以顺利有效施行的。第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涉及民间段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所承载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识形态诉求。尽管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但民众对转型期内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感受深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转折点在近一百年来并不多,历数起来大致是“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效应上近年表现逐渐明显。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商业浪潮和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切身体验,并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普遍的表达。与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相比,世纪之交前后的这20来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现代性体验。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很像西方社会之前经历的那种转型,只是我们在时间上滞后了而已。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些年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但有些地方用来形容中国社会近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亦有相似之处。如商品经济浪潮的推拥裹挟、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等都给人带来普遍的变动感,尤其是在这个急剧转型中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似未成熟——这从近年来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这一点给人带来很多的迷惘和焦虑。人们处在土地征用、拆迁、城市化等空间的迅速转变当中,处在拼命追赶“与时俱进”的各种不确定的事物变化当中,处在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失范诚信缺乏的危险境地当中,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浮躁和戾气当中……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总结回顾中,“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反观自身的时候,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种短平快且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俗文化形式——民间段子——在新兴电子传媒的推动下蓬勃兴起,人们在这些充满戏谑、狂欢、讽刺、自嘲的话语中深获共鸣。由于民间段子结构的松散性、主题的随意性、艺术的通俗性,几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创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衍化繁殖,体现出集体的智慧与趣味,再通过能够迅速传播的公共传播手段,使得人们同声相应,手、口、耳相传,最终形成一股全民狂欢的风气。在这种文化狂欢的背后,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无意识和平民意识形态的诉求,包含有一种无声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对权力压抑的消解。这可以从民间段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从内容上看,黄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与性器,带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话以及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的嘲讽。性与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属于禁忌的话题,禁忌的内容、禁忌的惩戒,意味在此之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力和制度权力。冲破这些禁忌,意味着一种抵抗和解放,并因此获得某种匿名的快感。这一点很像西方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的摇滚乐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摇滚乐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摇滚乐却得到不少赞赏,甚至文化研究的论者还把摇滚乐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摇滚乐的粗鄙、炫耀式的“堕落”,狂欢化和快感原则,甚至它的命运和遭遇,都跟黄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摇滚文化只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和肆无忌惮的“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话,中国近年盛行的民间段子则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狂欢文化。约翰·费斯克在论及大众文化的资本时曾指出:“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按照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权力给人的快感是双向的,“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无权的大众阶层很多时候喜欢通过低俗、鄙俗甚至淫秽的黄段子对道德话语权力进行挑战,以粗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带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意味。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使黄段子的讲述者与听众体会一种充满“机智”“巧妙”的创造性反应,获得“狡黠”“恶毒”的快感。如:一男子到医院做非典检查,护士取针刺手指为其验血,因一时没棉花,情急中护士赶紧将其手指含入口中。男子痴迷半晌后款款的说:我想再做个尿检。乡长穿着短裤作报告,讲到激动时把一只脚抬放在椅子上,小弟弟露了出来,会场一片哗然,他以为大家不耐烦,就大声说:这只是个头,后面还长着呢!以上几个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种符号,它不是叙事意欲突出的内容,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使叙事的氛围变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话语权力的整体沦陷中人们觉得亲密无间,有一种集体抵抗同一战线的快感。又如:政府做完工程却省下一大笔钱,于是众人开会举手表决。是把这笔钱拿来改造中小学还是改善监狱环境。会议分成两派,众人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老常委一语定乾坤:“你们这班子人这辈子还有机会上中小学么?”顿时众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决定改善监狱环境……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辨别真正成功人士: 1.没有名片;2.自己不开车;3.衣服没logo;4.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5.每天午睡;6.经常在郊区活动;7.包里现金很少……旁边一位农民兴奋地打断:“这种人,我们村全是!”以上两例是灰段子的常用叙事模式,用强烈的反差造成反讽,对权力符号的揶揄和解构,在听众的哄堂大笑中神圣、庄严的东西轰然倒塌。无权无势无财的大众在一无所有中往往只能通过灰段子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讽刺以及对权力符号的消解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嘲弄腐败官员、为富不仁的富贵者(他们一般被符号化为“贪官”“煤矿老板”“暴发户”等)的愚昧、无能、丑陋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体会一种对原权力进行嘲弄的权力,产生一种“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并“证实自身”,产生一种阶级认同,获得慰藉和温暖。这种精神胜利快感的表现形式在于民间段子独特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中激赏拉伯雷在笑谑民间文学收集和创作上的成就,他说:“人们一般提及,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性的地位。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 因此,拉伯雷被不少人指责,但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的、“鄙俗化”的风格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及民间获得解放的力量。而广场言语和狂欢化是民间笑谑文学的话语特点,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日常的、亦即非狂欢的生活中,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在这里)异化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群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 在论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阐发道:“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这种笑声是个矛盾体,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解放性)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现象的雏形——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段子所具有的广场言语和狂欢化的特点,决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种纯粹提供给人阅读的文本,其效果往往需要话语的讲述来呈现,具有一种“在场”性和“表演”性。“在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段子的讲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会上、旅行团的车上,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如网络论坛、QQ群、微信朋友圈等),起到一种交往和聚众狂欢的效果。“表演”性表现在讲述的时候注重模仿(行动、语气、口音等)、注重互动和即兴发挥。尽管很多民间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传播,但也只是为了扩散,作为聚众时候讲述做储备的“话本”。民间段子正因为有这种效果,成为大众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且有效的话语,在黄段子灰段子的讲述和哄笑声中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权贵或彻底低俗的情境中人们感觉到某种同一性,此时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得意失意,“人人回归自我”,获得一种“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民间段子的盛行就是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对权力的抵抗和对权力符号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会同时夹杂无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说明问题: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2012之前:我们用奶粉毁掉00后,考试毁掉90后,房价毁掉80后,失业毁掉70后,城管毁掉60后,下岗毁掉50后,拆迁毁掉40后,医改毁掉30后。(此处的“2012”源于美国2009年上映的灾难片《2012:世界末日》,引者注)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类段子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概括也许不够准确,甚至充满偏激,但说明了这些年人们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的同时,环顾四周,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势使人们对世界不断陌生化,连怀旧的时间和对象都找不到,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官员的腐败,社会诚信的缺乏,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热潮……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在餐桌酒酣之际,在同辈聚会之时,借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狂欢,为这些充满不满、忧惧、受挫的心灵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继续沉重的生活。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描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许把“宗教”改为“段子”亦有相通之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段子那么盛行的深层根源。二、规训与惩罚随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实上给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不少冲击,甚至给所谓“正统”道德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多来自文化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方意见代表带来了恐慌。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曾经出现过密集地讨伐黄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见认为,黄段子灰段子格调低下、庸俗无聊,甚至认为黄段子激发性欲导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黄段子定性为一种性骚扰等等。河北省深泽县纪委在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传播黄段子的文件中说,(黄段子)“低俗信息不仅毒害人的心灵、涣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蚀道德意识,已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甚至是腐败的温床”。2005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文件,严禁公务员在各种场合讲黄段子和传播黄段子,否则将被“处理”。2009年,河北深泽县竟然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6万余党员参与学习领会该县纪委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使用手机留存和传播“黄段子”的红头文件。报道称如经举报查实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和单位领导连带责任。 2006年,网络和各地方报纸上频频出现《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为标题的新闻,新闻说2006年3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其内容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73种增加至110多种,许多过去管理无凭、处罚无据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新法第42条明确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据说各地方政府又根据这条法规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细则,一时间“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讹传讹地得出 “传播黄段子是犯罪行为”、“发黄段子短信将被拘留”等说法,尽管有夸大和不实的成分,但多少也体现了官方的意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检查自己的手机,删掉手机上存留的涉嫌“黄”的短信。尽管后来未见有坐实案例报导,但“传播黄段子违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里,体现出统治者调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自发的民间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黄段子进行了一定成效的监管和遏制,采用的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手段。但由于这种监管和权力意志的过于强悍和独断,随之也引发了诸多在学理、法律层面的质疑与讨论。比如,如何确定黄段子与性骚扰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如何界定黄段子的标准等。有人提出这种监管会不会导致公权的滥用,如河北深泽县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是不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滥用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靠简单粗暴的禁止与惩罚似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给文化领导者出了一个难题。在这种局势下,红段子进入了文化领导者的视野,并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开创红段子短信大赛,大赛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抵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些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黄段子灰段子的负面影响而举办的。此后红段子短信大赛连续举办五年,全国多个省市都学习广东模式举办类似的红段子大赛。2010年2月11日,代表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以“手机红段子引领和谐文化”为题进行正式报道,将红段子命名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短信文化形式”。 2010年10月,《光明日报》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谁不说咱家乡好”的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红段子由个别的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表达升格到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高度,并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接管与推行。一时间红段子红遍大江南北,2009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该书在理论的高度给红段子进行了价值定位:“红段子掀起中国的红色新文化运动,”“我们应重拾汉唐盛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巨大影响力,创造网络时代风雷激荡的文化历史”。该书开宗明义“用‘红段子’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先破后立,意在‘主流话语权’”。 据此,红段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完成华丽转型。与民间自发的段子不同,红段子完全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诱导和规范(有奖征文比赛等方式)下进行的、并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传播的“仿”民间段子的话语形式。其话语方式是利用民间段子的表现形式,置换民间段子的内容,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确的政治观念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纳入其中,以达到“弘扬正气、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目的。红段子内容上多是励志短句、哲理箴言、节庆祝福之类,审美上尽量引导创造者(编写者)将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立场与人民大众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具有审美普遍性同时又具备党性原则的“红色新文化”。“‘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占领主流文化阵地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规训,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普遍运作原则。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询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具有一种“将个体询换为主体”的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一个或多个的观念赋予“主体”,这些关于“主体”的想象使主体直面个体,以个体的名义向赋予他想象性主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通过我称之为构建(interpellation)或呼叫(hailing)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或其他人)呼叫:‘喂!喂!’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recruits)主体(招募所有的个人)或者把个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体(改造所有的个人)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acts)或‘产生作用’(functions)的。” 红段子以充满人生哲理的劝世箴言、积极振奋的人生态度、温馨真诚的祝福话语共同构筑起一个关于和谐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不满与缺憾,引导民众参与并共同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前相互认可,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红段子要做的就是设法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使人们在关于温馨、美好、幸福、和谐的社会图景中达成共同的想象,并试图激发人民大众对生活对社会产生共同的向往和渴望进而实现审美交流,最终通过红段子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情感表达与当下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达成社会的和谐。在这里,红段子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们精神的领袖、生活的导师、知心的朋友、贴心的亲人……如: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则是一朵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湛蓝的天空,那么失意则是一片漂浮的白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大忧为国小忧为家。常怀博爱仁厚之心,待人诚挚待事圆滑。勿以己悲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处之。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摘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尊酒,但愿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试想,你的生活中经常被这些话语包围,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中,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幸福健康,让你感觉生活的美满,让你觉得人生值得一过,让你珍惜现在,安于现状……其实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幻象。在这里,红段子充当一种“新文艺”,它是一种既有哲理意味且同时饱含温情的情感性话语,具有一种审美的效果。根据文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识形态属性,马歇雷说,“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在某种意义上,审美的效果和意识形态的效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关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说:“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它是人类团结的源泉。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放任个体陷于孤独的自律,那就只有通过这种想象性的交流或相互适应的同一性,个体才能被紧密地结合起来。” 又说:“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以文艺审美的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情感性话语与政治意识等等之间产生和谐。红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黄段子灰段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伊格尔顿分析了审美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审美艺术品总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精神和感觉和谐地相互联起来”。基于美学的这个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效果:“主体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过教育和以实践为中介的欲望的理性教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导权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建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了情感在文化(政治)领导权争夺中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会内聚力能够形成的根源,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话语,从它产生之时就作为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强权的压迫,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这就是红段子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运作机制,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转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温和规训,应该说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呢?按主流媒体的报道,红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如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数度南下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行跟踪调研,并根据‘红段子’活动的实践与经验……历时一年”编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性成果《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再诸如《“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等标题可见一斑。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红段子的“伪”民间性,使得它在根源上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与民间段子的自发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实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和传播的红段子,则缺乏这些特质。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红段子情感苍白内容空洞,劝世箴言变成意识形态的说教,生活哲理成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很多红段子与流行歌曲唱的“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天天都是好日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其机械复制和没有明确对象的无限“群发”的特点,使红段子失去了真正的经验传达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应该离老百姓最为亲近的“真情祝福”的红段子来看,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性和针对性,在以短信“群发”的传送下变成一种空洞的祝福形式。如有一名学生在中秋节给我群发一个祝福:窗前明月光,秋风满庭芳;疑是地上霜,忽闻桂花香;举头望明月,即将中秋节;低头思念长,于是祝福忙:中秋将至,愿你月发幸福,月发健康!而另一名学生发这么一个祝福短信:“中秋将至,学生某某祝吴老师中秋快乐。”就表达形式而言,前者似乎显得更有审美性,更有情怀和诗意,更温馨美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成品,也许根本就没有祝福者个人的真正情感在里面,只是顺手的一个转发,而且我还知道他同时还发给了很多人,甚至在一天之内我会收到若干个与此一模一样的祝福信息。对比之下,后者的祝福尽管简单甚至简陋,但我知道这是指向我的、祝福者亲自输入的专属的一个情感表达,因此个人觉得后者更显得真诚一些。红段子如果没能具备民间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质,哪怕内容再健康、正确、积极、再“高大上”,也难以深入人心,最终只流于空泛,遭遇尴尬。三、僭越与和解作为主流文化领导者,面对无绪杂乱的民间俗文化形式的泛滥,要重树价值规范、扭转文艺方向,对低俗有害的自发文化进行抵制和引导,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抵抗的时候能想到文艺具有《毛诗序》里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抗衡、收编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夺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可取的。但官方意识形态在收编、整合和引导的时候应该遵循文艺的规律和原则。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而不考虑文艺自身的特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与打压,这一点值得商榷。从理论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的收编和规训,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损害。文化研究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文人对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改编、历代统治者对文艺的干涉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改造。户晓辉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或民俗”与作家收集整理出版的“文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差异之大达十多项,“但是,其中的差别还不止这些。一旦民间艺术被中产阶级作家和出版家挪用并且被变成以大众为中介的印刷形式,它就承受了剧烈的变化……它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角度就被泯没、丢失或置换了”。 同样道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段子的打压与规训,以民间段子形式置换出来的所谓红段子在很大程度上异质化了,最终红段子变成一种矛盾体。从文艺规律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僭越。就如当年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它以收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汇总和改编了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歌谣和打油诗。这种来自民间的歌谣按理说是最能够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心声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曾大量引用农民起义时期的各种歌谣和童谣来作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证据。但《红旗歌谣》在农业歉收和政策失误之下的中国民间却有“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等诸如此类的描述。这次活动显然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话语的一次现代的模仿,是以郭沫若和周扬为代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采风活动,现在看来是一次权力僭越的在文艺上收获不大的文化生产的浮夸行为。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红段子最终的效果;红段子没有推行之前,民间自发的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真的如文化领导者所说的那样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或性犯罪吗?这些民间段子真的对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构成威胁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谓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有话语权者对无话语权者的判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这个不赘述。至于说黄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这个则可以辩证来看。色情的文艺主要是激发人的性欲,指在文艺中对性交的细致描述、性器状况的描写以及性感受的铺排,但黄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作为符号或由头引发嘲讽或嘲笑的。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权力压抑的能量获得释放,既消解了权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说黄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发人的性欲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实践中很少有围听黄段子者性欲盎然的情况。如下面两个典型的黄段子:男知妻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听后气极说:“咱们也上床报复他俩!”事毕领导妻又说:“我还气,再报复一次!”一连三次,男跪倒趴下告饶:“求求你了,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一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检验结果出来了。但医院居然拿错了报告,误拿了孕妇的报告,检验结果怀孕了。男子看过报告后,迅速走到老婆面前,扇了老婆一个耳光!男子对老婆骂道:“我说我要在上面,你不干!偏偏你要在上面,这下,我怀孕了。” 以上这几个段子尽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并不是性本身,没有刻意赋予更多的性暗示,听众基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黄段子的叙事中,能指与所指往往是断裂的。另外,民间段子对官方意识形态有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冲动,但若说民间段子的流行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和实际威胁,这是不确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同时也很隐秘的自我修复和同化功能,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对另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抵抗,同时在抵抗的幻象式快感中就消解了对前者的实际反抗。亨利·吉罗等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中分析说:“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前面关于民间段子与红段子的分析也说明,他们的机制都是制造乌托邦,在最终的运作效果上基本是殊途同归的。最终来看,民间段子并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实质性的颠覆或占领,某种意义上还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固性。阿多诺就曾把大众文化当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稳固剂,是一种“社会水泥”。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间段子的娱乐消闲方式缓解了大众对社会的紧张感,反而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国在大众文化繁荣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是在“重视、支持、引导”的口号下对大众俗文化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间段子与红段子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层面上尽管方向不同,但最终被整体性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解与吸收,则是一样的,在某种高度上,他们达到了和解。所以,这次文化领导者对民间段子的恐慌与严厉,并以红段子来相抗衡争夺主流文化领导权,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也许在这次红段子的推导中,不乏权力的僭越的表现,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量与比拼,某县的480多场会议等,多是出于其他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寻租行为。另外,在红段子推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商业运作跟制度权力形成了合谋。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人为地制造对抗,意欲以强制性国家机器对黄段子讲述、传播进行惩罚,并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倡、领导、布置、审查、验收、整理作为文化生产方式的“红色新文化运动”也许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但是否也因此干涉或削弱了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呢?结语目前,一度曾经令有关部门担心会“黄祸”泛滥、世风败坏的黄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沉寂,红段子也由于它内在的空虚而又过于密集频繁地侵入人们的意识世界而被人故意地无视或无意地反感,也逐渐走向节制和沉默。综观这两类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博弈。我们还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抵抗和争夺,最终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归。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意识形态其实是人同现实联系的中介,是人对世界的感觉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表征,人们通过它,借以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启蒙与解放都来源于意识形态这个“表现系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这个“表现系统”进行分析,揭示它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深入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多了一种可能。[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吴高泉,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辑:若水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独立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摘要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关键词 黄段子;灰段子;红段子;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作为俗文化中最为贴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间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来以旺盛的生命力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近些年,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互联网的发达以及新兴便捷媒介手机、ipad等的勃兴,段子文化成为一种蔚为奇观的大众文化现象。然学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与政治等敏感话题而研究的不多,隐隐体现出一种不敢、不愿或不屑的心态。而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红段子”的言说,学界则普遍表现相对踊跃。较早从学术角度论及段子的是2008年《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上的一篇《段子管窥》,该文对段子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广义的段子,指的是个人或集体创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赏的、简短自足的或长篇中可独立出来的短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话、小品,也可以指戏剧中的唱段……狭义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尤其指近年来广泛流行的幽默类的故事、笑话、脱口秀、顺口溜等……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亦采用这个界定,所论的段子属于以上所说的狭义的段子。将近年流行的各类段子以颜色分为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等,既体现了人们对段子内容的区分也体现了价值判断的色彩。简言之,黄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为话题及取笑对象的段子,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灰段子指的是那些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抨击时弊或表达现实无奈的自嘲的段子,体现出一种灰色的心态或黑色幽默的特点;红段子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制作、传播的一种代表健康社会心理、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短信息文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与民间自发流传的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民众的精神空间,打击黄段子灰段子所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在段子的喧哗世界里,很典型地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和博弈。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这两大类具有对抗性质的段子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无意识和意识形态企图。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以上溯到20世纪文学批评中以文学的话语方式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这一传统摒弃了过去文学批评以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意图的臆测、抽象的美学特征、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而转向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进行“症候式”的阅读,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话语分析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多数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人民“真实”的情感表达,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对统治权力的某种抵抗,大众文化是差异文化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什么是大众文化,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大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MTV、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按照这个界定,中国内地近年流行的民间段子完全具备大众文化的特点,而且在表达的内容、创作的方式、传播的途径、意识形态的诉求等方面,比一般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如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更具有“大众”的身份和特点。因此,我们对当前大众文化中的这种代表形式——“段子”——进行话语分析,得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性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一、抵抗与消解要理解民间段子所表达的平民意识形态诉求,最好的方式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间段子(本文主要指黄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何以在中国内地盛行的原因。关于盛行原因,目前学界相关说法一般都比较务实,如《段子管窥》认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餐文化的消费;具有高度的娱乐性。《“黄段子”为何流行》认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绪放松的快乐,三是交友的需要。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娱乐、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艺术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与今天的段子内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艺现象,都可以说也具有以上所说的功用。明末冯梦龙《挂枝儿》《山歌》和《广笑府》里收集的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行“歌曲”和笑话有很多就属于今天理解的黄段子和灰段子。仅举几例:牙刷儿,身材短,刚刚五六寸,穿一领香喷喷绿背心。一条骨子儿生成的硬,短鬅松一搭毛儿黑,光油油好一个下半身。专与那唇齿相交也,(每日里)擦一阵儿爽快得很。昨夜同郎做一头,阿娘困在脚根头。姐道郎呀,扬子江当中盛饭轻轻哩介铲,铁线身粗慢慢里抽。姐儿生来像花开,花心未动等春来。囫囵囵两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里含羞夜里开。一僧读“齋”字,尼认是“齊”字,因而相争。一人断之曰:“上头是一样的,但是下头略有些差”。或问好色者曰:“世间何事最乐?”答曰:“行房最乐。”又问:“既行房后,还有甚乐?”沉吟曰:“除是再行。”官值暑日,欲寻避暑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凉。一皂隶曰:“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问其故,答曰:“此地有天无日头。”前面几则或隐或显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段子,其中第5则在当下被改成湖南或四川方言再次在民间流行(只是把“行房”改为“做爱”,最后一句改为“再做一次”)。第6则对有权者的讥讽则类似于今天的灰段子。如果单从民间文艺的一般功用角度来分析流行原因的话,似乎无法解释民间段子为什么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一层的追问,即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大量需要段子来消遣、娱乐、宣泄、交流?冯梦龙收集的这些大量涉及私情、欲望的民间“段子”在当时的盛行原因或可资参考。涉性的民间原生态的“段子”应该每个时代都有,只是过于“俚俗”“粗鄙”而不被文人收录和记载,它只能潜流于生活的当下,由于没有资料记载,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现冯梦龙这样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段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类似“段子”的大量流传。明末市民社会发达,民众的娱乐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于引起文人的关注,甚至介入收集、仿制和传播的行列;另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与当时新兴印刷技术的大众化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明显地强调其传播的“大众”、“消费”的媒介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民间段子近年在中国内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发达产生了其广泛的受众,最为关键的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明清时期的刊刻造纸技术对俗文化的推动一样,近年国内民间段子的盛行与新兴的互联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手机短信平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电子传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广,使民众广泛参与、广泛传播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种传媒交互平台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欢迎,客观上引导和鼓励了人们进行碎片式(“段”)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受众的审美体验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与黄段子灰段子相抗衡的红段子也正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平台得以顺利有效施行的。第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涉及民间段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其所承载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识形态诉求。尽管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但民众对转型期内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感受深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转折点在近一百年来并不多,历数起来大致是“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在社会效应上近年表现逐渐明显。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商业浪潮和急剧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给民众带来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切身体验,并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普遍的表达。与之前的几个转折点相比,世纪之交前后的这20来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现代性体验。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很像西方社会之前经历的那种转型,只是我们在时间上滞后了而已。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些年中,人们的普遍感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现代性体验,但有些地方用来形容中国社会近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亦有相似之处。如商品经济浪潮的推拥裹挟、城市化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等都给人带来普遍的变动感,尤其是在这个急剧转型中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似未成熟——这从近年来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明证——这一点给人带来很多的迷惘和焦虑。人们处在土地征用、拆迁、城市化等空间的迅速转变当中,处在拼命追赶“与时俱进”的各种不确定的事物变化当中,处在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失范诚信缺乏的危险境地当中,处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浮躁和戾气当中……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总结回顾中,“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反观自身的时候,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种短平快且符合人们情感表达的俗文化形式——民间段子——在新兴电子传媒的推动下蓬勃兴起,人们在这些充满戏谑、狂欢、讽刺、自嘲的话语中深获共鸣。由于民间段子结构的松散性、主题的随意性、艺术的通俗性,几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创者,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衍化繁殖,体现出集体的智慧与趣味,再通过能够迅速传播的公共传播手段,使得人们同声相应,手、口、耳相传,最终形成一股全民狂欢的风气。在这种文化狂欢的背后,蕴含有深刻的文化无意识和平民意识形态的诉求,包含有一种无声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对权力压抑的消解。这可以从民间段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现出来。从内容上看,黄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与性器,带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话以及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的嘲讽。性与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属于禁忌的话题,禁忌的内容、禁忌的惩戒,意味在此之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力和制度权力。冲破这些禁忌,意味着一种抵抗和解放,并因此获得某种匿名的快感。这一点很像西方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的摇滚乐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摇滚乐曾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摇滚乐却得到不少赞赏,甚至文化研究的论者还把摇滚乐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摇滚乐的粗鄙、炫耀式的“堕落”,狂欢化和快感原则,甚至它的命运和遭遇,都跟黄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摇滚文化只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和肆无忌惮的“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话,中国近年盛行的民间段子则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狂欢文化。约翰·费斯克在论及大众文化的资本时曾指出:“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按照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权力给人的快感是双向的,“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无权的大众阶层很多时候喜欢通过低俗、鄙俗甚至淫秽的黄段子对道德话语权力进行挑战,以粗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带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意味。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使黄段子的讲述者与听众体会一种充满“机智”“巧妙”的创造性反应,获得“狡黠”“恶毒”的快感。如:一男子到医院做非典检查,护士取针刺手指为其验血,因一时没棉花,情急中护士赶紧将其手指含入口中。男子痴迷半晌后款款的说:我想再做个尿检。乡长穿着短裤作报告,讲到激动时把一只脚抬放在椅子上,小弟弟露了出来,会场一片哗然,他以为大家不耐烦,就大声说:这只是个头,后面还长着呢!以上几个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种符号,它不是叙事意欲突出的内容,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只是为了使叙事的氛围变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话语权力的整体沦陷中人们觉得亲密无间,有一种集体抵抗同一战线的快感。又如:政府做完工程却省下一大笔钱,于是众人开会举手表决。是把这笔钱拿来改造中小学还是改善监狱环境。会议分成两派,众人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老常委一语定乾坤:“你们这班子人这辈子还有机会上中小学么?”顿时众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后举手表决,一致决定改善监狱环境……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辨别真正成功人士: 1.没有名片;2.自己不开车;3.衣服没logo;4.没有小区名,只有门牌号;5.每天午睡;6.经常在郊区活动;7.包里现金很少……旁边一位农民兴奋地打断:“这种人,我们村全是!”以上两例是灰段子的常用叙事模式,用强烈的反差造成反讽,对权力符号的揶揄和解构,在听众的哄堂大笑中神圣、庄严的东西轰然倒塌。无权无势无财的大众在一无所有中往往只能通过灰段子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讽刺以及对权力符号的消解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嘲弄腐败官员、为富不仁的富贵者(他们一般被符号化为“贪官”“煤矿老板”“暴发户”等)的愚昧、无能、丑陋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体会一种对原权力进行嘲弄的权力,产生一种“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并“证实自身”,产生一种阶级认同,获得慰藉和温暖。这种精神胜利快感的表现形式在于民间段子独特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中激赏拉伯雷在笑谑民间文学收集和创作上的成就,他说:“人们一般提及,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本身、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绝对压倒性的地位。这些形象还以非常夸大的、夸张化的方式出现。” 因此,拉伯雷被不少人指责,但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的、“鄙俗化”的风格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及民间获得解放的力量。而广场言语和狂欢化是民间笑谑文学的话语特点,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日常的、亦即非狂欢的生活中,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在这里)异化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群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 在论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伊格尔顿阐发道:“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这种笑声是个矛盾体,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解放性)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现象的雏形——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段子所具有的广场言语和狂欢化的特点,决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种纯粹提供给人阅读的文本,其效果往往需要话语的讲述来呈现,具有一种“在场”性和“表演”性。“在场”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段子的讲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会上、旅行团的车上,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如网络论坛、QQ群、微信朋友圈等),起到一种交往和聚众狂欢的效果。“表演”性表现在讲述的时候注重模仿(行动、语气、口音等)、注重互动和即兴发挥。尽管很多民间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传播,但也只是为了扩散,作为聚众时候讲述做储备的“话本”。民间段子正因为有这种效果,成为大众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且有效的话语,在黄段子灰段子的讲述和哄笑声中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权贵或彻底低俗的情境中人们感觉到某种同一性,此时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得意失意,“人人回归自我”,获得一种“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民间段子的盛行就是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结果。除了对权力的抵抗和对权力符号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会同时夹杂无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说明问题: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2012之前:我们用奶粉毁掉00后,考试毁掉90后,房价毁掉80后,失业毁掉70后,城管毁掉60后,下岗毁掉50后,拆迁毁掉40后,医改毁掉30后。(此处的“2012”源于美国2009年上映的灾难片《2012:世界末日》,引者注)中国人的科学启蒙: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里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类段子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概括也许不够准确,甚至充满偏激,但说明了这些年人们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生存状况的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的同时,环顾四周,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势使人们对世界不断陌生化,连怀旧的时间和对象都找不到,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官员的腐败,社会诚信的缺乏,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热潮……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在餐桌酒酣之际,在同辈聚会之时,借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狂欢,为这些充满不满、忧惧、受挫的心灵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继续沉重的生活。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描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许把“宗教”改为“段子”亦有相通之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段子那么盛行的深层根源。二、规训与惩罚随着黄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实上给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不少冲击,甚至给所谓“正统”道德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多来自文化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方意见代表带来了恐慌。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曾经出现过密集地讨伐黄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见认为,黄段子灰段子格调低下、庸俗无聊,甚至认为黄段子激发性欲导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黄段子定性为一种性骚扰等等。河北省深泽县纪委在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传播黄段子的文件中说,(黄段子)“低俗信息不仅毒害人的心灵、涣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蚀道德意识,已成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甚至是腐败的温床”。2005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文件,严禁公务员在各种场合讲黄段子和传播黄段子,否则将被“处理”。2009年,河北深泽县竟然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6万余党员参与学习领会该县纪委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干部使用手机留存和传播“黄段子”的红头文件。报道称如经举报查实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和单位领导连带责任。 2006年,网络和各地方报纸上频频出现《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为标题的新闻,新闻说2006年3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其内容中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73种增加至110多种,许多过去管理无凭、处罚无据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新法第42条明确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据说各地方政府又根据这条法规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细则,一时间“乱发黄段子可拘留10天”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讹传讹地得出 “传播黄段子是犯罪行为”、“发黄段子短信将被拘留”等说法,尽管有夸大和不实的成分,但多少也体现了官方的意志。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检查自己的手机,删掉手机上存留的涉嫌“黄”的短信。尽管后来未见有坐实案例报导,但“传播黄段子违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里,体现出统治者调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自发的民间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黄段子进行了一定成效的监管和遏制,采用的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手段。但由于这种监管和权力意志的过于强悍和独断,随之也引发了诸多在学理、法律层面的质疑与讨论。比如,如何确定黄段子与性骚扰的关系,如何有效保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如何界定黄段子的标准等。有人提出这种监管会不会导致公权的滥用,如河北深泽县组织480多场专题讨论会是不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滥用等问题。在此形势下,靠简单粗暴的禁止与惩罚似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给文化领导者出了一个难题。在这种局势下,红段子进入了文化领导者的视野,并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开创红段子短信大赛,大赛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抵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些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以积极向上的内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黄段子灰段子的负面影响而举办的。此后红段子短信大赛连续举办五年,全国多个省市都学习广东模式举办类似的红段子大赛。2010年2月11日,代表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以“手机红段子引领和谐文化”为题进行正式报道,将红段子命名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短信文化形式”。 2010年10月,《光明日报》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举办主题为“谁不说咱家乡好”的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红段子由个别的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表达升格到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高度,并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接管与推行。一时间红段子红遍大江南北,2009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该书在理论的高度给红段子进行了价值定位:“红段子掀起中国的红色新文化运动,”“我们应重拾汉唐盛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巨大影响力,创造网络时代风雷激荡的文化历史”。该书开宗明义“用‘红段子’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先破后立,意在‘主流话语权’”。 据此,红段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完成华丽转型。与民间自发的段子不同,红段子完全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诱导和规范(有奖征文比赛等方式)下进行的、并动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传播的“仿”民间段子的话语形式。其话语方式是利用民间段子的表现形式,置换民间段子的内容,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确的政治观念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纳入其中,以达到“弘扬正气、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目的。红段子内容上多是励志短句、哲理箴言、节庆祝福之类,审美上尽量引导创造者(编写者)将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立场与人民大众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具有审美普遍性同时又具备党性原则的“红色新文化”。“‘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占领主流文化阵地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的规训,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普遍运作原则。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提出的“询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具有一种“将个体询换为主体”的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把一个或多个的观念赋予“主体”,这些关于“主体”的想象使主体直面个体,以个体的名义向赋予他想象性主体的意识形态认同。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通过我称之为构建(interpellation)或呼叫(hailing)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或其他人)呼叫:‘喂!喂!’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recruits)主体(招募所有的个人)或者把个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体(改造所有的个人)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acts)或‘产生作用’(functions)的。” 红段子以充满人生哲理的劝世箴言、积极振奋的人生态度、温馨真诚的祝福话语共同构筑起一个关于和谐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对抗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不满与缺憾,引导民众参与并共同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在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前相互认可,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红段子要做的就是设法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使人们在关于温馨、美好、幸福、和谐的社会图景中达成共同的想象,并试图激发人民大众对生活对社会产生共同的向往和渴望进而实现审美交流,最终通过红段子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把情感表达与当下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达成社会的和谐。在这里,红段子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们精神的领袖、生活的导师、知心的朋友、贴心的亲人……如: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则是一朵骤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说人生是湛蓝的天空,那么失意则是一片漂浮的白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大忧为国小忧为家。常怀博爱仁厚之心,待人诚挚待事圆滑。勿以己悲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处之。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摘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尊酒,但愿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试想,你的生活中经常被这些话语包围,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间最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中,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幸福健康,让你感觉生活的美满,让你觉得人生值得一过,让你珍惜现在,安于现状……其实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幻象。在这里,红段子充当一种“新文艺”,它是一种既有哲理意味且同时饱含温情的情感性话语,具有一种审美的效果。根据文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识形态属性,马歇雷说,“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在某种意义上,审美的效果和意识形态的效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关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说:“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它是人类团结的源泉。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放任个体陷于孤独的自律,那就只有通过这种想象性的交流或相互适应的同一性,个体才能被紧密地结合起来。” 又说:“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以文艺审美的方式来表达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情感性话语与政治意识等等之间产生和谐。红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黄段子灰段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伊格尔顿分析了审美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审美艺术品总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精神和感觉和谐地相互联起来”。基于美学的这个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效果:“主体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过教育和以实践为中介的欲望的理性教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导权的过程,人们才能不断地建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了情感在文化(政治)领导权争夺中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会内聚力能够形成的根源,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话语,从它产生之时就作为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中介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强权的压迫,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这就是红段子话语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运作机制,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严厉惩罚转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温和规训,应该说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呢?按主流媒体的报道,红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如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课题组,数度南下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行跟踪调研,并根据‘红段子’活动的实践与经验……历时一年”编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性成果《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再诸如《“红段子”映照中国大地》、《“红段子”掀起红色文化浪潮》等标题可见一斑。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红段子的“伪”民间性,使得它在根源上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与民间段子的自发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实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和传播的红段子,则缺乏这些特质。在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红段子情感苍白内容空洞,劝世箴言变成意识形态的说教,生活哲理成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很多红段子与流行歌曲唱的“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天天都是好日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其机械复制和没有明确对象的无限“群发”的特点,使红段子失去了真正的经验传达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应该离老百姓最为亲近的“真情祝福”的红段子来看,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性和针对性,在以短信“群发”的传送下变成一种空洞的祝福形式。如有一名学生在中秋节给我群发一个祝福:窗前明月光,秋风满庭芳;疑是地上霜,忽闻桂花香;举头望明月,即将中秋节;低头思念长,于是祝福忙:中秋将至,愿你月发幸福,月发健康!而另一名学生发这么一个祝福短信:“中秋将至,学生某某祝吴老师中秋快乐。”就表达形式而言,前者似乎显得更有审美性,更有情怀和诗意,更温馨美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成品,也许根本就没有祝福者个人的真正情感在里面,只是顺手的一个转发,而且我还知道他同时还发给了很多人,甚至在一天之内我会收到若干个与此一模一样的祝福信息。对比之下,后者的祝福尽管简单甚至简陋,但我知道这是指向我的、祝福者亲自输入的专属的一个情感表达,因此个人觉得后者更显得真诚一些。红段子如果没能具备民间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质,哪怕内容再健康、正确、积极、再“高大上”,也难以深入人心,最终只流于空泛,遭遇尴尬。三、僭越与和解作为主流文化领导者,面对无绪杂乱的民间俗文化形式的泛滥,要重树价值规范、扭转文艺方向,对低俗有害的自发文化进行抵制和引导,应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抵抗的时候能想到文艺具有《毛诗序》里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抗衡、收编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夺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可取的。但官方意识形态在收编、整合和引导的时候应该遵循文艺的规律和原则。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而不考虑文艺自身的特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与打压,这一点值得商榷。从理论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的收编和规训,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损害。文化研究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文人对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改编、历代统治者对文艺的干涉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改造。户晓辉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或民俗”与作家收集整理出版的“文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差异之大达十多项,“但是,其中的差别还不止这些。一旦民间艺术被中产阶级作家和出版家挪用并且被变成以大众为中介的印刷形式,它就承受了剧烈的变化……它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叙述角度就被泯没、丢失或置换了”。 同样道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段子的打压与规训,以民间段子形式置换出来的所谓红段子在很大程度上异质化了,最终红段子变成一种矛盾体。从文艺规律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僭越。就如当年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它以收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汇总和改编了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歌谣和打油诗。这种来自民间的歌谣按理说是最能够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和心声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曾大量引用农民起义时期的各种歌谣和童谣来作为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现的证据。但《红旗歌谣》在农业歉收和政策失误之下的中国民间却有“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等诸如此类的描述。这次活动显然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话语的一次现代的模仿,是以郭沫若和周扬为代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采风活动,现在看来是一次权力僭越的在文艺上收获不大的文化生产的浮夸行为。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红段子最终的效果;红段子没有推行之前,民间自发的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真的如文化领导者所说的那样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或性犯罪吗?这些民间段子真的对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构成威胁吗?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谓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有话语权者对无话语权者的判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傲慢,这个不赘述。至于说黄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骚扰,这个则可以辩证来看。色情的文艺主要是激发人的性欲,指在文艺中对性交的细致描述、性器状况的描写以及性感受的铺排,但黄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作为符号或由头引发嘲讽或嘲笑的。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权力压抑的能量获得释放,既消解了权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说黄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发人的性欲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实践中很少有围听黄段子者性欲盎然的情况。如下面两个典型的黄段子:男知妻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听后气极说:“咱们也上床报复他俩!”事毕领导妻又说:“我还气,再报复一次!”一连三次,男跪倒趴下告饶:“求求你了,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一男子去医院检查身体,检验结果出来了。但医院居然拿错了报告,误拿了孕妇的报告,检验结果怀孕了。男子看过报告后,迅速走到老婆面前,扇了老婆一个耳光!男子对老婆骂道:“我说我要在上面,你不干!偏偏你要在上面,这下,我怀孕了。” 以上这几个段子尽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并不是性本身,没有刻意赋予更多的性暗示,听众基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黄段子的叙事中,能指与所指往往是断裂的。另外,民间段子对官方意识形态有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冲动,但若说民间段子的流行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和实际威胁,这是不确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同时也很隐秘的自我修复和同化功能,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对另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抵抗,同时在抵抗的幻象式快感中就消解了对前者的实际反抗。亨利·吉罗等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中分析说:“为了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现存的传媒现象的多功能,评价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层属性变得十分必要。除了影视中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前面关于民间段子与红段子的分析也说明,他们的机制都是制造乌托邦,在最终的运作效果上基本是殊途同归的。最终来看,民间段子并没有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实质性的颠覆或占领,某种意义上还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固性。阿多诺就曾把大众文化当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稳固剂,是一种“社会水泥”。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间段子的娱乐消闲方式缓解了大众对社会的紧张感,反而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国在大众文化繁荣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是在“重视、支持、引导”的口号下对大众俗文化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间段子与红段子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层面上尽管方向不同,但最终被整体性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解与吸收,则是一样的,在某种高度上,他们达到了和解。所以,这次文化领导者对民间段子的恐慌与严厉,并以红段子来相抗衡争夺主流文化领导权,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也许在这次红段子的推导中,不乏权力的僭越的表现,如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量与比拼,某县的480多场会议等,多是出于其他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寻租行为。另外,在红段子推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商业运作跟制度权力形成了合谋。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人为地制造对抗,意欲以强制性国家机器对黄段子讲述、传播进行惩罚,并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倡、领导、布置、审查、验收、整理作为文化生产方式的“红色新文化运动”也许强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但是否也因此干涉或削弱了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呢?结语目前,一度曾经令有关部门担心会“黄祸”泛滥、世风败坏的黄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沉寂,红段子也由于它内在的空虚而又过于密集频繁地侵入人们的意识世界而被人故意地无视或无意地反感,也逐渐走向节制和沉默。综观这两类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博弈。我们还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抵抗和争夺,最终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归。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意识形态其实是人同现实联系的中介,是人对世界的感觉方式,是现实生活的表征,人们通过它,借以表达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启蒙与解放都来源于意识形态这个“表现系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这个“表现系统”进行分析,揭示它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深入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多了一种可能。[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作者:吴高泉,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辑:若水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独立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